器官移植为人类医学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不但让受者的生命得以延续,也让施者的奉献精神永垂不朽,是一项造福社会、荫及后人的善举。从佛教的伦理观点来看,器官捐赠也是一种舍身救人的菩萨行,从大量的佛典中确实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丰富教证。然而,器官捐赠与佛教净土宗所倡导的临终指南产生了冲突。净土宗认为人在断气后,神识尚未离体,故还有知觉作用,如此时妄动遗体,将会引发“瞋心”,加剧亡者的痛苦而影响其投生善趣。该主张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不少佛教徒和民间信众陷入了到底要利他的“舍己救人”,还是要自利的“安详往生”的两难抉择,影响了其捐赠意愿。为拨开迷雾,太和智库研究员释慧固法师翻阅大量文献,从“临终八小时勿触遗体”之说的起源及其变迁过程入手,从学理上对此“冲突点”进行剖析,站在学理的高度和历史的长度来反思其不合理之处。由于篇幅所限,脚注及文献原文稍有节略。

器官捐赠的议题曾在佛学界引起不少讨论,其中大多研究以印光大师的《临终三大要》和弘一大师的《人生之最后》作为切入点,围绕“临终后有无知觉”的问题进行辨析,而没有在历史上往前探寻渊源,也未对其变迁的过程进行梳理。本文将力求从文献追溯源头,并从中看待整个演变过程。
“临终八小时勿触遗体”之说为近代净土宗所倡导。经(指《众经撰杂譬喻》)言:“阿耆达王,立佛塔寺,功德巍巍。临终,侍人持扇,误坠王面,王起一念瞋心,死后即堕蛇身。后遇沙门说经,闻法乃得生天。”大多数研究认为,正是因为仆人将扇子坠在临终的阿耆达王脸上,触碰了其遗体,才导致阿耆达王因瞋而堕蛇身。这一故事也成为临终勿触遗体的重要佐证,常常被净土宗的著作引用来证明这一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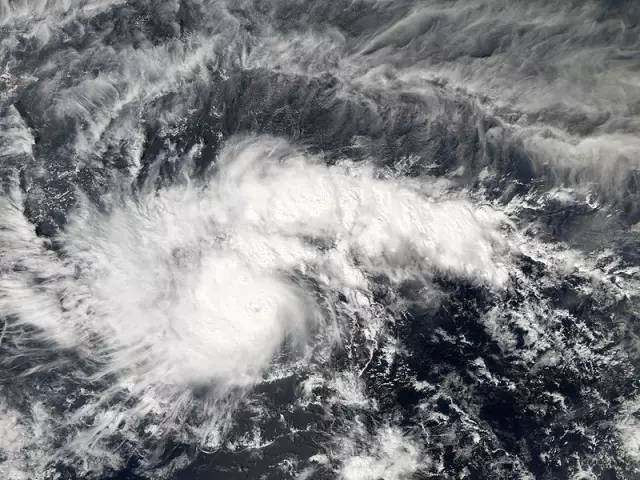
顺治年间净土宗著作《净土晨钟》中有一篇短文《饬护病者》,文中强调,“临终侍人(相当于看护)不可不护病者心”,因为“至于终时,惹瞋惹恋,误亡者入他道,尤可惧也”,即当人临命终时,如果生起贪念、瞋心,就会堕入恶道。
到了咸丰年间,净土宗的另一部著作《劝修净土切要》,其附录篇《临终舟楫要语》提出,人断气后,遗体若有余温,则第八识尚未离体,亡者仍有知觉,此时切忌穿衣、盘膝搬动亡者,免其因痛生瞋,堕入恶道。倡言需待通身死透(暖尽),确定主人翁(识)已去后,再迟两三时(4~6小时),方可浴洗穿衣,这是首次提出从断气后到能触碰遗体之间的间隔时间。
随后在同治年间,又出现了一部《净土极信录》,其中《看护沉疴助终往生诀》篇和《将终西行含酸难忍语》篇详细阐述了僧人临终前后的注意事项。《看护沉疴助终往生诀》篇着重于对临终者的看护,指出病人临终之际,因“四大分张,八苦交煎”而坐卧不安,此时应任凭其“斜倚歪靠、伸脚盘腿”,不要挪动身体,致其动念;在临终几刻,看护者更应该用心照顾,为其念佛,须念到浑身冷尽,暖气全无,之后再为其浴身洗面、换衣,停七天之后,才能焚化遗体。《将终西行含酸难忍语》篇则以唯识学理论和“寿暖识三者常不离相”的经教阐释为何七天之后才能焚化的理由。因为临终时,前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渐次而去,只有第七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要等到第七天才能去尽;若身体稍有一暖,则彼识未去,既未去尽,仍知痛苦;勉强搬动亡者,易令其生起瞋心,致其堕落,所以一定要等到七天之后才能火化遗体。

到了近代,印光大师在其著名的《临终三大要》里,对病人临终前、临终时和临终后三个时段提出了三项要点: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联系前文可以发现,这“三大要”在前述文献中均有提及,第三大要中提及的“切戒搬动哭泣”、“不可洗澡、换衣”、“彼如何坐卧,只可顺彼之势”,与《劝修净土切要.临终舟楫要语》和《净土极信录.看护沉疴助终往生诀》中的“切忌穿衣,盘膝搬动”、“由他扑眠、仰卧、斜倚歪靠、伸脚盘腿,种种奇形异相,听凭他使,不宜挪移”和“勉强搬动、盘腿等事亦复难受”等叙述不谋而合,而且三篇文章对于此要的解释均类似于“将终之时,身不由主”、“一动则手足身体,均受拗折扭裂之痛,痛则瞋心生,随瞋心去,多堕毒类”。总的来看,《临终三大要》对如何劝人念佛、如何助念的指导相比于《劝修净土切要.临终舟楫要语》和《净土极信录.看护沉疴助终往生诀》更为详细、系统。
随后,弘一大师进一步扩充临终关怀指南,写了《人生之最后》一文。相比于《临终三大要》,弘一大师的《人生之最后》中的临终关怀更为细致,将临终后的关怀指南细化为“命终后一日”和“七七日”两个阶段。更值得关注的是,弘一大师明确提出了人从断气后到可以触碰遗体的时间间隔为“八小时”,此说一经提出便开始广为流传,影响至今,就形成了时下所闻的“临终八小时勿触遗体”。

综上,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近代净土宗所倡导的“临终八小时勿触遗体”一说来源于17世纪的净土宗著作《净土晨钟•饬护病者》。深究发现,其与明末崇祯年间弘赞法师针对《四分律》所著的《四分律名义标释》存在紧密联系。原因有二:1、《四分律名义标释》与净土宗著作《净土晨钟》、《劝修净土切要•临终舟楫要语》、《净土极信录》、《临终三大要》和《人生之最后》都用阿耆达王因瞋堕蛇的故事作为“临终不可触碰遗体”的依据;2、《四分律名义标释》的“往生十方佛剎土”、“临终之日…洗浴身体,着鲜洁之衣,烧众名香,悬缯旛盖,歌赞三宝,读诵尊经”的思想与净土宗的往生教义相符合,因此被净土宗所接受也不足为奇。
梳理清楚了源起及发展脉络,我们得知临终不得触碰遗体的思想与做法是在清代随着净土宗普遍流行后才出现的。值得一问的是,在佛教诸多派系里,为什么惟独近代净土宗才会有这个避讳呢?反观一些教派,如︰南传佛教(斯里兰卡)的僧众们热烈积极响应器官捐赠的活动;北传佛教的星云大师以身作则签署器官捐赠卡以及台湾慈济功德会发起的骨髓捐赠运动等等。难道同为佛门中人,他们不认同“阿耆达王因瞋堕蛇”的诫训吗?面对这种差异甚大的态度,佛教弟子当依于何理来抉择?对于临终前后有无知觉所提出的理论依据,这些论证在学理上到底能否站得住脚呢?是故必需一一审视核验方可知晓。
诚如所述,“临终八小时勿触遗体”一说是把整个焦点放在了临终前后有无知觉的问题上,是依于清代出现的几部净土宗著作里头所引用的唯识学理论和寿暖识三者常不离相的经教展开的,所以“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由此,从“识”的层面入手解析是最佳门径。

根据佛法的基本教义──“十二缘起”(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位于第三支的“识”和第四支的“名色”之间的关系犹如束芦,是展转相依而得竖立的,这里须加注意的是它们的内容。一般把第四支的“名色”作为概括一切精神与物质之总称。自语意而言,“名”是精神的作用,指的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简称“六识”;“色”是物质的作用,指的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简称“五根”。除了“名(六识)”之外,十二缘起还单独立了一个位于第三支的“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这个“识”与“名(六识)”是不同的精神层次,正确来说,第三支的“识”相当于更为核心的生命中枢。对此,佛典云︰“无明覆,爱结系,得此识身”,这“识”说的就是“名(六识)”之外的“有取识”。佛教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中,各个派别对此“识”有着不同的立名,比如︰大众部称之为“根本识”;唯识学派称之为“阿赖耶识”、“阿黎耶识”或“阿陀那识”。《摄大乘论本》、《唯识三十论颂》中均详细说明了此“识”是根本识,有别于均有生灭的前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而前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有时生起,有时不起(或俱或不俱);第六识(意识)在正常的时候虽然不间断(意识常现起),但是当修习禅定达到念想灭尽,仅存色身及不相应行蕴的无想定和灭尽定(除生无想天,及无心二定)时,或在沉睡与昏厥的时刻(睡眠与闷绝),意识在这个时候完全是中止的。那么问题来了:当意识中止时,为什么身体的各种机能并没有因此而停顿,新陈代谢仍然照常运转?简言之,就是人为什么还是活着的?合理的解释是︰还有一个更深细的生命作用存在,它执受着色根,所以身体不需要心念的指挥,就能够自动职司新陈代谢的种种功能,比如︰呼吸、消化等等。这些都是前六识功能之外的生命作用,职司此一生命中枢功能者,也就是上述所说位于十二缘起中第三支的“识”──执受根身的作用。佛典中对“识”的解释大致如此。接下来,为了方便撰文及解说,下文将以“阿陀那识”作为这个职司生命中枢功能的统称。
死亡的定义有多种,依道统的说法,无呼吸、无心跳、颈动脉搏动消失等等身体机能的完全停止即是死亡。但从佛法的观点来看,这些状态不一定就是死亡,一些修习禅定成就第四禅者在入定的时候,也会出现上述情形。由于这其中的理论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故此不再展开论述,我们就单单依于道统上的死亡定义,结合“识”的问题切入讨论。

话说回来,照“执受”的原理来推论︰死亡后,身体的机能全面停息,是因为阿陀那识已经停止了“执受根身”的作用。此识正作用时,是与体温(暖)和命根(寿)互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就是所谓的“寿、暖、识三者常不离相”之说。这三者必须互相依持,生命方可得以持续,反之则死,恰如油、炷、灯火,三者缺一不可。在《成唯识论》里,唯识学派依于《阿含经》里“识缘名色,名色缘识”的经教就作出了论证,认为若命根(寿)断绝了,阿陀那识就会舍离根身;识既不再执受色身,那么身体上所有的机能,诸如︰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免疫系统、呼吸等等作用就会完全停止。少了这些,色身就会转变成冷冰冰的尸体,开始呈腐烂败坏之象。所以如果死亡以后,身识仍然有觉受的作用,进而还能够导致意识生起贪瞋痴等烦恼,那就表示阿陀那识并没有舍离根身。依此类推,阿陀那识没有舍离根身则表示“执受根身”的功能依然还在,那么身体上所有的机能就不会停止;心脏依然跳动,血液就会循环,体温(暖)就不会冷却;免疫功能依旧发挥作用,身体也不会因此而腐烂败坏。总的来说,职司生命中枢的阿陀那识执受与否是划分生与死的界线──执受时,寿与暖俱在;舍离时,寿与暖俱灭。至此,寿暖识的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答,紧接着要处理的,就是阿陀那识到底是如何与痛苦、瞋怒等觉受情绪产生关联的呢?
首先,身体之所以会有知觉感受,是因为六识里的身识发挥着作用。如前面所说,六识是生灭间断的,它们依于阿陀那识而转起,当阿陀那识执受根身时,它们就会随缘俱转。但如果阿陀那识舍离根身,六识便不会转起。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如此来说──有阿陀那识者,前六识不一定会转起;可是,只要有前六识的生起,其背后肯定是有阿陀那识作为依持。所以当一个人已经死亡,阿陀那识不再执受根身,六识也不再起任何作用时,亡者还会因被摘取器官感到痛苦进而生起瞋怒,这就说不通了。别说死亡,只要处在深度昏迷(或弥留)状态,甚至在手术台上用麻醉剂将神经系统传输觉受的功能切断,病患连意识和知觉能力都会宣告失效,类同于“闷绝”,怎么还会产生瞋怒等情绪呢?
综上,我们以唯识学理论阐述了“识”的功能,得出结论是︰人在脑死亡后,命根已败坏(寿已尽),阿陀那识失去执受功能,六识因而不起作用,所以撷取器官时是不会产生痛觉的。除了从学理上辨析外,笔者认为清代出现的文献以及文献中引用的阿耆达王因瞋堕蛇的故事存有更为关键的问题,需要展开深入反思。

(一)对文献的反思
对《劝修净土切要.临终舟楫要语》的质疑点有二:其一,其言“佛制亡僧焚化...如今释子以焚化了事,不依制度,往往停龛一日,即行焚化,则大违佛制可乎”,里头的“不依制度”指的是什么制度呢?经由细究,此言其实出自《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主要从三个方面推断︰首先,就时间顺序,《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的成书时间早于《劝修净土切要》,前者是清道光年间,后者是清咸丰年间;其次在语句上,《劝修净土切要.临终舟楫要语》开头的“佛制亡僧焚化,原为令其离分段之假形,而证真常之法身”与《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的“佛制亡僧烧化者,令其离分段之假,而证常住之法身也”只存在些许差异;再者,自唐代以后,以禅宗《百丈丛林清规》为核心的寺院僧团管理制度成为佛教各宗各派遵守的规范,一直沿用至今,僧团内大大小小的事都包含在清规内,从生到死皆有一套如法的规范,因此净土宗藉其临终部分作为参考亦非不可能。若判断无误,《劝修净土切要.临终舟楫要语》实际上就是参照了《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的部分内容而成文,并非依于律典提出“制度”一说,也就是说《劝修净土切要.临终舟楫要语》参考的根本不是“第一手文献”。
此外,若沿着内容来看,仪润法师在《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里就“荼毘”一事,先简略说明佛制已逝僧人必须火化,原因在于破除其对色身的执着、倦恋,并喝斥一些畏惧火化的僧人,后续的论述完全顺着“亡僧必须火化”充分展开。然而,《劝修净土切要.临终舟楫要语》前文引用了《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的这个说法,后文却就“亡僧不可停龛一日即行焚化”的原因展开论述,可见与《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的原意是存在一定出入的。

其二,《劝修净土切要.临终舟楫要语》倡导“不能只停龛一日即行焚化”的原因是深怕亡者意识尚未离去而遭遇火焚之苦,同时也叮咛不要帮其更换衣物及盘膝搬动等,但后面又说“待通身死透,则主人翁(识)已去,再迟两三时,方可浴洗穿衣”。何以得知“通身死透”呢?如文中所言,“必待通身冰冷,无一点暖气”,也就是等到遗体完全冷却之时。正常情况下,遗体完全冷透的时间只需数小时,此后就可“浴洗穿衣”。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遗体“冰冷”就算完全“死透”,那为何还忌“不能只停龛一日”呢?这难道不奇怪吗?
更难以理解的,是随后把《劝修净土切要.临终舟楫要语》的逻辑思路连同问题等一并继承下来的《净土极信录》。在这基础上,《净土极信录.将终西行含酸难忍语》还补充说“识”离开的时间是七天,所以将停龛几日具体明确为“七日”后方可火化。这种说法会产生几个疑问:如果“识”需要七天去尽,那是不是需要等七天之后才能为亡者浴身洗面?若依通身冰冷的标准,我们假设亡者断气后十小时内,遗体就完全冰冷,此时是否可以判定其“识”已离开?如果“是”,那么能否帮亡者浴身洗面了?如果“不是”,那“通身冰冷”一说不就无法成立吗?追问下去,如果遗体“冰冷”就算完全“死透”,那还需要忌讳停龛几日的问题吗?或是,假设七天后遗体仍没变冷,是不是还得继续放着不得浴身洗面和火化了……细阅了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其逻辑思路、理论、论证依据等疑点重重,说法令人匪夷所思,实在难以让人明白何者可以作为准则,得出的结论是:由此发展出来的“临终八小时勿触遗体”一说确实值得怀疑和检讨。
(二)对阿耆达王故事的反思
始于弘赞法师的《四分律名义标释》,到后来问世的几本净土宗著作里,皆以“阿耆达王因瞋堕蛇”作为核心依据,并以唯识学和寿暖识三不离相的学理为辅,大力倡导临终不得触碰遗体的思想。虽然前面我们从学理的部分已经得到解答,但如何用来解释阿耆达王的事例呢?因为他确实是在临终之际,在旁侍人持扇误堕其脸上,才导致他瞋火怒发,然后堕入蛇身。因此,学理上的论证再怎么强而有力,阿耆达王的故事仍然是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了支持不触碰遗体的有力证据,进而影响了器官捐赠的推动。但笔者认为,把这故事套到“临终后勿触遗体”一事上面来谈其实是欠妥的。

首先,阿耆达王是属于自然死亡,有别于脑死,与大多器官捐赠者有所不同。佛教以四大分解来描述迈向死亡(一般指正常的自然死亡)的过程,根据佛典的说法,这过程犹如“生龟脱壳”般难受。在自然死亡的情况下,临终者会经历从意识清醒到进入弥留两个阶段,直至最后完全死亡(四大分解结束为止)。当意识清醒时(前六识尚有作用),临终者会如生龟脱壳般难受,此时“盘膝搬动”身体,易让其产生负面情绪,这类似于常人受病痛折磨时,若被外界打扰,极易心烦意乱;而当进入弥留状态时,如前文所述,意识和知觉能力几乎已丧失,是不会引发知觉的情绪反应,好比方说当人被扼住咽喉时会有难受之感,数分钟后,大脑因缺氧进入昏迷状态,此时前六识会完全停止作用(感觉顿消)。虽然意识与知觉丧失,但前面挣扎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则会被继承下来。以此推断,阿耆达王那一瞋念的生起应是在历经四大分解的过程中,处于尚未进入弥留状态之前的意识清醒阶段,并不符合临终八小时的条件设定。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从其原文的叙述来看,“我(阿耆达王)临命终时,边人持扇堕我面上,令我瞋恚,受是蛇身”,里面只说扇子堕王面后,令王生起“瞋恚”,并未说明阿耆达王是因“痛”而生瞋。众所周知,能够引发瞋恚的原因有诸多,比如︰不满、不如己意、嫉妒等等。从阿耆达王生瞋一事来看,也不排除在当时的等级制时代,奴隶的任何失误都被视为是对王的一种冒犯、大不敬的行为,这也不无可能。但后人在引用该故事时,可能多受到“四大分张、八苦交煎、生龟脱壳”等观念影响,直接将生起“瞋恚”的原因推向“因痛生瞋”,未免太过片面。
由于受到近代净土宗“临终八小时勿触碰遗体”理论的影响,当面对要不要支持器官捐赠的抉择时,就会出现正与反两种声音。支持的一方常常引用“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功德无量”、“功不唐捐”等作为回应,却鲜有站在学理上来论证者,因此说服力不大;而不鼓励器官捐赠的一方引用教界大德的观点,充分以“临终不得触碰遗体”的思想全面否决器官捐赠的可行性。经由本文讨论,我们找到了“临终八小时勿触碰遗体”的源头,并看到了整个演变的过程,从中也看出所依据的文献及所使的学理,存有一种曲解原意的嫌疑。由此可知,捐赠遗体之事善莫大焉,无须有过多顾虑。
太和智库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太和智库,关注时代需要。
微信公众号:taihezhi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