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22年10月16日,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
中华文明作为唯一延续至今、未曾间断的古代文明,在治国理政方面留下了大量智慧结晶。不夸张地说,处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核心命题。有别于西方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对立的做法,中华文明致力于实现国家与人民的和谐统一;在国家对待人民的问题上,中华文明推崇“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的民本思想;在人民对待国家的问题上,中华文明则孕育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3]的家国情怀;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华文明还为这份家国情怀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不同时代的普通百姓只要通过军功爵制、察举制、科举制遴选,就能实现修齐治平[4]的理想。
中国共产党人生于长江,长于黄河,对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耳濡目染,已将不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同马克思主义思想贯通起来,运用到日常工作中。例如,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致力于实现国家与人民的和谐统一,还始终坚持党的人民立场,牢记中国共产党人“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5]。中华文明所推崇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中焕发新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6]。中国共产党人还通过行动实践了中华文明所提倡的家国情怀,当神州大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不断沉沦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齐聚于南湖红船,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1949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也继承了中华文明用制度哺育“天下兴亡”责任感的智慧结晶,人民共和国的每位公民都有机会通过公务员考试和党组织的考察,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同时,党和政府还建立了完备的教育制度,普通公民即便不参与治国平天下,也能获得修身齐家所需的国民教育。
本文旨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即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入手,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基础,找出那些早已被中国共产党人同马克思主义思想贯通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7],先秦有卜筮[8]军国大事的传统。《易经》作为卜筮书,承载着先贤关于治国理政的大量思考。例如,《易经·乾卦》就借由阐述天道运行的原理,说明了处理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基本原则:
乾:元亨利贞。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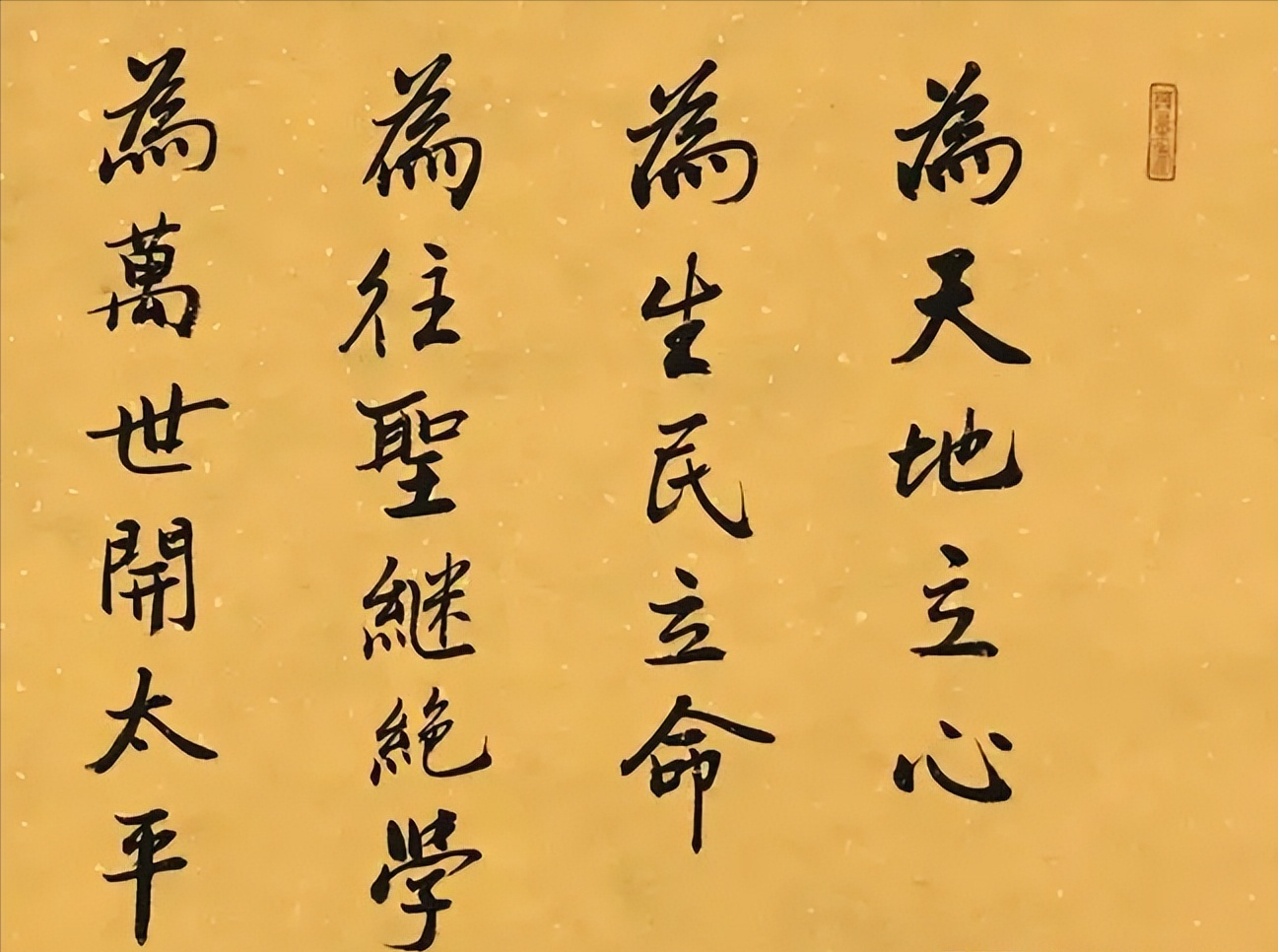
《周易正义》认为,天道有“纯阳之性”,能够孳生万物,并赋予万物相应的特性和寿命。唯有让天道处于至高的和谐状态,万物才能得其利而又不失其正。同样的道理投射到人世,君主唯有致力于实现国家与人民的和谐统一,确保其臻于“太和”,天下才能太平。
翻阅史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深深根植于神州大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甚至可追溯到上古三代。《古文尚书[9]·夏书·五子之歌》有云: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大禹[10]的王位世袭到孙辈时,发生了“太康[11]失国”的重大变故。夏王太康虽身居王位,但却不理政事,耽于享乐,夏朝百姓都不再拥戴他。然而太康不仅不思悔改,还远赴洛水南岸游猎,过了百日都不回到国都。有穷氏部落的首领后羿[12]见夏朝百姓再也无法忍受这位夏王,遂发兵洛水北岸,阻止太康回国。事后,太康的五位兄弟逃出国都,在洛水转弯处追述祖父大禹的教导,反思“太康失国”的缘由。太康的其中一位兄弟悲歌道:祖父大禹曾教导我们,绝不能轻视百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唯有根本牢固了,国家才会安宁。我治理百姓时总是心怀戒慎恐惧,如同在用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烈马。太康贵为天子,又岂能不对百姓心怀敬意呢?
继《五子之歌》之后,商汤[13]讨伐夏桀[14]、周武[15]讨伐商纣[16]的誓词也从侧面体现了时人的民本思想。《今文尚书·商书·汤誓》有云: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商汤在誓词中坦言,一部分商人不大理解他讨伐夏桀的决定。他们纷纷抱怨道:为何我们的君主不体恤自己的百姓,宁可荒废本国的农事,也要讨伐夏王?鉴此,商汤特地在誓词中解释了他讨伐夏桀的理由:不是我胆敢犯上作乱,而是上天看到夏王犯下太多罪过,命令我起兵夏王。夏王耗尽民力,剥削百姓。夏朝百姓对他不再恭敬,与他的关系也不复融洽,甚至愿与他同归于尽。夏王的君德已沦丧至此,我必定要去讨伐夏王。不难看出,不论是主张讨伐夏桀的商汤,还是对此感到不解的一部分商人,其立论基础都是民本思想。在他们看来,“我后”是要“恤我众”的,亦即君主要体恤百姓。
《今文尚书·周书·牧誓》又云: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周武王在誓词中强调,他讨伐商纣王是在恭行天罚,而商纣王的一大罪状就是尊敬重用四方逃亡而来的罪恶多端之人,任命他们为大夫、卿士,结果这些罪恶多端之人向百姓施加暴行,在商邑肆意作乱[17]。
民本思想传承到西周初年,发展出中华文明特有的民本主义天命观。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神明常常因为国君不够虔诚而降下灾祸,中华文明的上天则关心国君是否力行德政,否则就会终结他的天命,转移给其他有德之人。
虽然后世常常把商汤讨伐夏桀和周武讨伐商纣并称为“汤武革命”,但两场革命的难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殷周鼎革之际,周人的实力和在诸侯间的威望都远逊于夏朝末年的商人,就连周人自身都惊讶于“小邦周”竟然能战胜“大邑商”,西周初年商人掀起的三监之乱[18]更是商朝初年的夏人所未能做到的。然而,也正是这如履薄冰的政治现实,迫使周公[19]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发明出了民本主义的天命观。
《今文尚书·周书·多士》有云:
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若曰:“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
周公将反抗周朝统治的殷遗民迁到成周,并以周成王[20]的名义对他们进行告诫。反复咀嚼《多士》的文字,不难看出周人虽然两次征服了商人,但仍不敢小看这群殷遗民,反而煞费苦心甚至屈尊纡贵地劝说他们。周公深谙语言的艺术,他首先试图降低殷遗民的抵触情绪,强调殷周鼎革是天意所致:帝辛不敬重上天,导致上天向商朝降下丧乱;周人只是尊奉上天的旨意,宣告商朝的天命终结于帝辛。不是小小的周国胆敢终结商朝的天命。倘若上天不从信诬怙恶的帝辛手中取回天命,转而保佑周人,周人又岂敢奢求天子之位呢?随后,周公为加强自身的说服力,还推己及人地论证夏殷鼎革也是天命转移所致,正因为上天终结了夏桀的天命,商汤才得以取代夏桀成为天子。

经过上述铺垫,周公才最终提出上天转移天命的标准:从商汤到帝乙[21],没有一位商王不力行德政,慎行祭祀。反观帝辛,既不敬畏天意,也不遵循先王的教导,上天这才不再保佑商朝,降下了如此大的丧乱。上天不会把天命授予不力行德政的君主。四方之内,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的灭亡,都是上天的惩罚。不难看出,周公天命观的内核正是民本思想,即天子唯有力行德政,才能保住天命。然而,所谓天意终究是世人的想象,周公其实有意无意地以上天为中介,将统治者的合法性间接地归于人民。
中华文明特有的民本主义天命观传承到东周秦汉之际,逐渐从统治者解释王朝鼎革的学说,发展成儒家劝说君主力行德政的天人感应思想。春秋时,王室衰微,孔子[22]周游列国十四年,未能扭转礼崩乐坏的时局,只得将未竟的政治理想寄托到整理六经[23]的工作中。例如,孔子在编撰史书《春秋》时,就常常将王公贵族的所作所为与灾异祥瑞相编排,暗示人祸与灾异间的因果关系。在孔子看来,上天每逢人祸都会降下灾异作为警告,而人君唯有改正错误的政策才能破除灾异。
上博简[24]《鲁邦大旱》记载了孔子向鲁哀公[25]“推销”天人感应思想的故事:
鲁邦大旱,哀公谓孔子:“子不为我图之?”孔子答曰:“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庶民知说之事鬼也,不知刑与德。如毋爱圭璧币帛于山川,正刑与德[26]。”
《鲁邦大旱》成书于战国时代,虽然其记载的未必是孔子的真人真事,但多少反映了天人感应思想在当时的发展。相传鲁国遭遇大旱,哀公特向年迈的孔子请教应对之策。孔子顺势提出:莫非是刑德出了问题?但百姓都习惯通过祭祀鬼神来平息大旱,不甚了解刑德与大旱的因果关系。国君您不如一面祭祀山川,一面端正刑德之治。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春秋时代的孔子,还是战国时代的儒生,都深知天人感应思想太过超前,需要有所折衷才能被时人接受。因而,孔子生前多将天人感应思想付诸《春秋》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鲁邦大旱》中的孔子也一改“不语怪力乱神”[27]的形象,先是建议哀公顺应民俗,“如毋爱圭璧币帛于山川”,尔后才劝说哀公“正刑与德”,破除大旱的真正原因。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山川鬼神祭祀和天人感应思想都是封建迷信,但考虑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若要求时人对天灾成因有科学的认识,反而不大现实。如此一来,我们对两者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自然只能以结果论。由此观之,春秋战国时大多数人信奉的山川鬼神祭祀虽有抚慰人心之效,但“性价比”缺乏保障;而儒家发明的天人感应思想则试图将天灾用作敦行德政的工具,把坏事变成好事,即便是封建迷信,也是秉持民本思想、心系百姓福祉的封建迷信。

经过几代儒生的努力,天人感应思想才成为主流思想。战国时,齐人公羊高[28]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其说后被汇编为《春秋公羊传》。汉儒董仲舒[29]钻研公羊学,进而在《举贤良对策》中向武帝[30]系统性地“推销”了天人感应思想: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31]。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指出,《春秋》中关于天人感应的记载“甚可畏也”,但上天的本意还是爱护天子的,只要不是“大亡道之世”,上天都会竭力制止乱政,让天下尽可能免于“伤败”;每逢“国家将有失道之败”,上天都会先降下灾害“谴告”天子;如果天子“不知自省”,上天就会降下更严重的怪异,进一步“警惧”天子;如果天子至此“尚不知变”,上天才会最终降下“伤败”。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被武帝采纳,对传统时代的中国政治乃至此后两千年的中华文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自秦始皇[32]“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33],历代帝王都驾驭着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士大夫作为官僚机器的一分子,若想要拦阻皇帝施行乱政,就少不了意识形态的“武装”。而天人感应思想的妙处恰恰在于,其抓住了天子受命于天的合法性来源,让士大夫可以拿灾异说事,谏言皇帝改行德政。
中华文明在政治上极为早熟,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完成了“天下兴亡,天子有责”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超越。炎黄子孙习惯了国家与人民之间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往往在无意识间忽略了“天下兴亡,天子有责”才是其他古代文明的常态。事实上在西方,直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后,国家与公民之间才建立了如此紧密的联系。
春秋时,王室衰微,“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34],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天下兴亡,天子有责”向“天下兴亡,诸侯有责”的超越。姜齐虽是协助周革殷命的元勋,但到西周中叶便饱受周天子的打压,周夷王[35]甚至听信谗言,烹杀齐哀公[36]。然而到了华夏共同体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齐桓公[37]并未选择独善其身,而是不计前嫌地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九合诸侯,救援燕国,重建邢卫,逼退楚国,维系了春秋初年的天下秩序和礼乐文明。
我们唯有回到春秋初年的政治现实,才能理解“天下兴亡,诸侯有责”的历史意义。当时的华夏共同体可谓是进退维谷,一方面周天子失去宗周故地,龟缩在伊洛平原,已无力领导诸侯抵御“蛮夷”与楚国的进攻,维系华夏共同体的天下秩序和礼乐文明;另一方面齐晋等诸侯国虽然实力雄厚,但都不具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威信。这也就意味着,必须要有诸侯国挺身而出,在无法取周天子而代之的情况下,履行周天子的大部分职责,为其他诸侯国提供名为“天下秩序”的公共产品,捍卫华夏共同体的礼乐文明,甚至要做兴灭继绝的“赔本生意”。而正是齐桓公肩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履行了远超其身份的责任,为其他诸侯乃至士大夫起到了榜样作用。
回到“天下兴亡”责任感不断拓展开来的正题。春秋中期,“尊王攘夷”失去了维系天下秩序、捍卫礼乐文明的初衷,反倒沦为晋楚两国的争霸战争。地处晋楚两国之间的中原各国更是频频沦为战场,遭遇生灵涂炭的厄运。既然王室衰微,天子暗弱,诸侯又不以天下苍生计,“天下兴亡”的重任自然进一步落到了卿大夫身上。先是公元前579年,宋国大夫华元[38]善用其与晋执政栾书[39]和楚公子婴齐[40]的私交,促成第一次弭兵之盟,维持了数年的和平。后是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41]召集晋楚齐秦等十三国代表达成第二次弭兵之盟,以中原小国同时向晋侯、楚王进贡为代价,换来了晋楚及中原各国四十余年的和平。除两次弭兵之盟外,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虽然未能扭转礼崩乐坏的时局,但未尝不是“天下兴亡,大夫有责”的一次伟大尝试。

战国时期,“天下兴亡”的责任感进一步拓展开来,大夫以下的士人也开始奔走于列国间,实践诸子百家的治国理想。当然,这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春秋时期,生产力逐渐发展,士阶层在维持生计外,也有了学习知识的余裕。孔子等较为开明的卿大夫兴办私学,有教无类,打破了知识的藩篱。于是,修齐治平的理想不再是大夫的特权,而逐渐在士阶层中传播开来。更重要的是,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还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华文明是最擅长用制度解决问题的文明。在“天下兴亡”的责任感从大夫向“匹夫”演进的过程中,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士阶层的经济条件远逊于大夫,没有世卿世禄的制度保障,即便士阶层怀有修齐治平的一腔热血,也总不能让其长年累月地进行无私奉献。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恰恰解决了这一难题,打破了世卿世禄的藩篱,允许士人凭借功劳实现阶层跃迁。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秦国的商鞅[42]变法,其一大改革便是建立军功爵制,将军功与出仕机会、经济待遇等关键权利直接挂钩:即便是平民百姓,“能得甲首一者”,也能“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43];即便是公族外戚,若无军功,也不得列入宗室,享受特权;而所有官吏,都必须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
不夸张地说,秦国之所以能实现统一,恰恰是因为商鞅变法用军功爵制哺育了秦国百姓的家国情怀,为他们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提供了切实的制度保障。换作近数十年流行的西方话语,商鞅变法不啻为秦孝公[44]与秦国百姓缔结的“契约”,只要愿意上战场建立军功,就能获得实现修齐治平理想的机会和保障。此后,即便孝公病逝、商鞅车裂,历代秦国君主乃至秦朝皇帝也都信守着这份“契约”,直至秦朝覆亡。
当然,将军功爵制作为联系国家与人民的主要纽带,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承秦之制的西汉就曾因此陷入两难。汉初与民休息,少有征战,结果阶层流动陷于停滞,从高帝[45]至武帝中年的丞相大都是功臣侯及其子弟[46]。反之,武帝北击匈奴,东并朝鲜,南诛百越,西征大宛,促进了阶层流动,提拔了一批平民子弟,打破了汉初功臣侯垄断相位的格局。但到了武帝晚年,国力空耗,百姓疲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竟险些重蹈亡秦覆辙。就连《汉书·武帝纪》都不禁感叹,“赞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更好的制度。既然将军功爵制用作家国情怀的制度保障会引发两难,无法做到“保合太和”、实现国家与人民的和谐统一,中华文明自然会呼唤新的制度,而由此应运而生的正是察举制。汉初便常常诏举贤能,但多是偶尔为之,没有明确的察举期限、人数、标准,直到武帝朝才发生根本变化。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公元前140年,暨武帝即位第一年,便“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但此举受到了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所举之士都被戴上“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的帽子,被迫罢归。公元前134年,暨太皇太后窦氏[47]病逝翌年,武帝便开始用制度解决问题,“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明确了郡国必须向朝廷推荐的人数,正式开启了察举制。然而守旧势力仍进行消极抵抗,“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武帝对此大为恼怒,于公元前128年下诏将郡国不举孝廉上升为“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的政治问题,要求“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最终后者奏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察举制这才得到落实,逐渐推广开来。
倘若说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是秦孝公与秦国百姓订立的第一份“契约”,察举制便是汉武帝与汉朝百姓订立的第二份“契约”。自此以降,士人都有可能凭借自身的品德和才能获得郡国举荐,进而获得出仕机会,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并获得相应的物质保障。此后,即便武帝驾崩、汉朝覆亡,通过禅让继承汉朝天命的中古帝王也无不信守着这份“契约”,将察举制作为联系国家与人民的主要纽带。
当然,察举制也并非尽善尽美,只要是推荐就避免不了主观因素。虽然察举制也常采用策试的形式,但总体上仍是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策试本身也远非制度化和严密化。西晋以降,皇权式微,选官制度甚至成为了门阀贵族的玩物,只看重家世门第,偏离了任人唯贤的原则。直到隋朝重振皇权,一统宇内,朝廷才有机会重新用制度解决问题。隋炀帝[48]发明科举制,开启了以考试取士的传统。自此往后一千四百年,以考试取士、相对客观的科举制取代了以推荐取士、相对主观的察举制。炎黄子孙大都有感于宋儒“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49]的家国情怀,往往忽略了联系庙堂与江湖、朝廷与百姓的制度纽带正是科举制。
不夸张地说,科举制不啻于隋炀帝与隋朝百姓的第三份“契约”,隋清之际的士大夫都有可能凭借自身才学,在科举考试中过五关斩六将,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虽然杨隋的天命只禅让到赵宋,元明清都通过暴力手段实现鼎革,但科举制仍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隋清之际的历代帝王莫不遵守着这份“契约”。甚至有学者认为,清朝之所以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迅速土崩瓦解,恰恰是因为其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切断了联系朝廷与百姓的制度纽带,就连尚且支持君主制的士大夫也感到寒心。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使命。中华历史文化学者、研究者亟需重拾儒家经世致用的理想,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将它们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贯通起来,进行守正创新,积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马克思主义者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思想贯通起来,不先把握其中的意旨是行不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动辄便可追溯到上古三代,而先秦时代的文言文确实太过晦涩难懂,常常是每个字都认识,但连成一句话,就是读不懂。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必因此气馁,就连传统时代的儒生也得仰仗注释才能读懂先秦时代的儒家典籍[50]。马克思主义者们只要肯下苦功,掌握经典的注释体系及学术源流,便能得其门而入。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家都有其生活的时代,中华文明更讲究经世致用。历代儒生在以何种方式解读经典的问题上从未泥古不化,而会自觉不自觉地顺应时代需要。例如,《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合称《春秋》三传,当汉武帝以铁腕推进“大一统”时,公羊家为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当西汉后期转向仁德之治时,重视礼乐教化的谷梁家自然响应了时代的呼唤。不夸张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历史,就是一部守正创新史。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就必然能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根深叶茂!

中国共产党人日用而不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浩如烟海,等待着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贯通起来的中华文明智慧结晶也灿若星辰。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应俯身躬耕于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一面平整土地,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一面兴修水利,将马克思主义的清流引入田中,进行守正创新,最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
注释:
